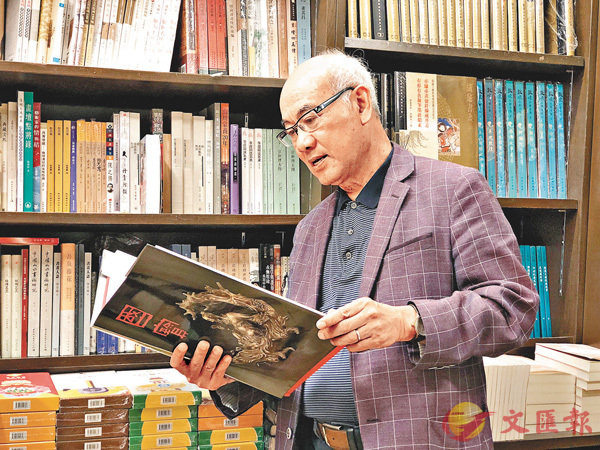 ■陳萬雄。尉瑋 攝
■陳萬雄。尉瑋 攝香港商務印書館與故宮博物院的緣分始於35年前出版的大型畫冊《紫禁城宮殿》。在精美的文化畫冊闕如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編輯團隊從外國的畫冊出版中吸取靈感,從人文、藝術的角度來走近紫禁城,走近國寶,編撰出學術與普及性並重、雅俗共賞的故宮畫冊。今年,香港商務更推出十卷英文版的《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集》,將故宮文化再一次推向世界。
聯合出版集團前總裁陳萬雄三十多年前加入香港商務,他說,自己最重要的出版正是從故宮開始。■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陳萬雄加入了香港商務印書館。他自小對文化感興趣,在日本學習時最愛就是逛書店。當時日本出版業正值興盛,書店之多,書店之好,讀書風氣之炙熱,都讓陳萬雄興奮不已。他用「美輪美奐」來形容當時日本的出版盛況。「70年代之間,日本出了很多大型的畫冊,重要的出版社更是每年都有特別的規劃。這也因為當時彩色印刷剛開始進入發達時期,技術的進步帶動了出版的風潮。」所有的這些,都對他有很大的刺激。
陳萬雄回到香港時正值中國內地剛剛開放,全世界都向這個曾經與外界阻隔的東方國度投射出好奇的目光,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如果要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要怎麼出書,才能令到海外的中國人、華僑,或是外國人感興趣呢?」陳萬雄不停琢磨,而日本的經驗告訴他,畫冊,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從遭冷遇變貴賓
當時香港商務有一份雜誌叫《風光》,介紹內地的風土人情,也不時有關於中國文化、故宮文物的文章。「我們覺得既然世界上有這樣的潮流,不如將雜誌裡面關於故宮的文章圖片編輯成畫冊,帶出去世界。」圖錄的樣書做出來,陳萬雄滿懷希望地到日本去向出版社推銷,卻遭到了冷遇。「當時也覺得很委屈的,但也激發了我的信念。」他笑着說,「我們的圖冊,不論攝影、印刷等各方面都和日本當時的出版要求距離太遠了。但以中國的文化、文物、風景,我們絕對可以做出一本國際性的書!」
回到香港,他對時任聯合出版集團總裁的李祖澤說:「除非不想打入國際市場,不然一定要有國際市場的水平!」李祖澤對陳萬雄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於是香港商務動用大量的財力和人力,專門組織攝影團隊前往北京,與故宮合作拍攝大型畫冊,這就是1982年面世的《紫禁城宮殿》。陳萬雄回憶道,當時光攝影師的人工每日就高達700港元,整個團隊更在北京拍攝兩月有餘,「這樣的出版項目,香港的出版社還沒人試過。」
《紫禁城宮殿》一出版,立刻在香港造成轟動,第一版印了7000多冊,三個月內就已售罄。「當時定價400塊一本,很多人的薪水那時也才每月1000左右。」不僅在香港賣得好,也售出了多種外文版權,北京故宮亦將這本書作為贈送外賓的禮物。1986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訪問中國參觀故宮,外交部長吳學謙就以此書作為禮物送給英女王,成為一段佳話。
帶着這本書重新「殺」回日本的陳萬雄,可謂「一雪前恥」。「我再去日本,去見幾間最大的出版社,講談社、小學館、學研社、中央公論社等。先見了講談社,他們答應出2000本。接着我去中央公論,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樓,樓下是小小的會見室。編輯見了我,一翻完書,就問我可不可以上二樓,去見畫冊的編輯主任。我到了二樓,主任看完後就說讓我去三樓,找總編輯。總編輯看完後很感興趣,又讓我上四樓見社長。社長看完很快拍了板。」說起這段經歷,陳萬雄仍是忍不住莞爾,但雖然在中央公論享受了「步步高陞」的美運,畫冊的最終版權仍是給了講談社,「雖然中央公論給的印數多,但是對當時日本來說講談社是NO.1,包括他們出的畫冊都是不得了的。給他們,對我們的書和香港商務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為大眾編撰畫冊
《紫禁城宮殿》的成功牽起了香港商務與故宮的不解緣,隨後出版的《國寶薈萃》、《國寶》、《清代宮廷生活》,又或是再次轟動出版界的六十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逐步奠定了香港商務在文化藝術畫冊領域的領先地位。陳萬雄說,當時的出版「正趕上了好時機」,「文革十幾年的封閉,讓大家對中國的發展很有興趣,對中國文化很渴望。而八十年代時香港已經進入現代發展,產生了一批中產階級,他們對文化品位和知識追求有要求。另外,很重要的,香港八十年代時已成為日本以外印刷水平最好的地方。所有的這些條件,再加上我們攝影的美觀、故宮的全力以赴等,促成了書的成功。」
然而除了天時地利的加持,故宮畫冊的成功,還得益於其出版方向的專業把握。陳萬雄心心念念的,是將中國藝術文化闡述給現代讀者看,不僅給國內讀者看,還要走向世界。「以往的畫冊出版,要不就是美術書,要不就是文物書,都是比較專業的角度和學術的範疇。但我們是用一個大眾文化的角度,用文化閱讀的方式去做的。這個出版風氣可謂是香港商務帶動的。」他說,「一方面當時我們在香港很有優勢,我們有很多英文書店,英美出了很多很漂亮的畫冊,我們可以看到。另外我在日本也看了很多很美的書。雖然沒有人教,但看得多了,慢慢就得到啟發,了解現在外國的閱讀潮流。回到香港後,我也經常去書店打書釘,躲在裡面看大型畫冊。當時,建築和藝術是畫冊中很重要的主題,我就看西方怎麼編畫冊,怎麼去呈現教堂、城市、古建築,自己去摸索編輯構想。像在《紫禁城宮殿》,我們會有整體的建築理論,也有具體的建築佈局,甚至最後還講到美術設計的圖樣pattern等細節,當時沒有人這樣去演繹中國的古建築。可以說我們是發揮了香港的優勢去做。」
為了拍出宮殿原本的樣貌,攝影組清晨五點入宮,晚上八點出宮,盡全力捕捉宮殿的「無人」狀態。更甚者,拍攝前要花大工夫移去欄杆等現代的擺設,又或是除去院落角落的雜草,盡全力突出建築原始的美感。
另一角度看建築
但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中國建築中的藝術與文化內涵,在和故宮的合作中也曾發生分歧。最典型的一次,陳萬雄在日本出差時被緊急召到北京,原來攝影團隊和故宮因為太和殿的拍攝角度問題鬧僵了。「他們不滿意我們的攝影師將太和殿用廣角的角度,或仰拍的方式來表現,而認為拍攝皇宮就要用正正經經的,方正平穩的角度。我就很耐心地解釋,建築是藝術,這本書不是完全講皇宮的,我想表達的是中國的建築藝術。太和殿我們已經拍了一張很正方的,但這表達不了其背後的人文意念。比如百官匍匐在太和廣場下面,皇帝端坐在太和殿上面,龍椅已經很高了。從大臣的眼來看太和殿,是怎麼一個震懾的作用?我們要捕捉的就是背後的這個理念。」最終故宮方面同意了出版團隊的意見,最終收錄在《紫禁城宮殿》中的照片,從不同的角度傳達出不同的氛圍,人與建築的關係,被巧妙地體現出來。
除了照片,書中所配的文字亦有一番推敲。「坦白說,以往寫畫冊的專家、大學者,是從專業出發去寫,他們不知道以文化閱讀角度出發的畫冊,要target的不是專業人士,而是相對普通的讀者。比如《國寶》,我很感謝朱家溍先生,他寫的每一件文物的條目,每一篇都是很精細的小文章,我很欣賞,但普通人可能會覺得深。於是我寫信給他,向他解釋我們畫冊的設想,是希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不管你讀什麼科,通過這本書,都能認識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與藝術。他很好,就全部再寫過。不是我們的學問比他高,文字比他好,而是作為出版人,要令海內外的讀者都能看明白,我們要去引導專家。」
陳萬雄說,作為出版人,最大的樂趣就是可以接觸各個領域的專家,學習大量的各種知識。他笑說自己是天生的編輯和出版人,對任何的學科,編書時都大量閱讀。做完《紫禁城宮殿》,他便感歎要是當時選讀建築該多好。十卷英文版《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集》面世,走向世界的夢想又進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在編撰英文版的過程中他發現香港有着絕佳的翻譯人才,既通中英,又對中外文化都有深厚的理解。「香港真的有我們的優勢。」他篤定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