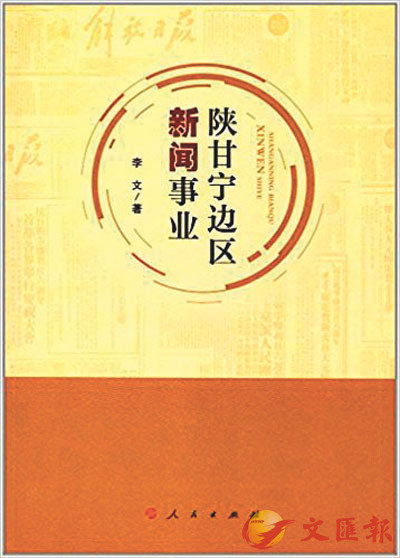
�m���̹���Ϸs�D�Ʒ~�n
�@�̡G����
�X�����G�H���X����
��Ǧ~�ӡA�u���w�ɴ��v��s�v���������@�ҥv�B��ǥv�B�F�v�v�B���|�v�B���N�v�B�s�D�Ǽ��v�ѾǬ�@�P���`���@�ӷs���C���F�z�Q�a��Ū���w�ɴ������v�����A�H�̶}�l��v�ơB���跽�y�B�����M�D�A��@�ӤQ�T�~�����v�����A�v���a�٭�F�X�ӡC
��Ѫ��O�A�����������Ī����w�ɴ��s�D�Ǽ��v��s�A�o�ܤ��S���@�����㪺�u���w�ɴ��s�D�Ǽ���ƥv�v�C2017�~5��A����бª��s�ۡm���̹���Ϸs�D�Ʒ~�n�ש�X���F�A�u���w�ǡv���Шt�o�ͤF���c�ʪ����ܡA�����M���A�s�D�Ǽ��Ǭ���o�F���@�w�����w�ɴ���s���ܻy�v�C�n���O�A�ѩ�U�Ǭ줧�����q�O�X�@�A�u���w�ɴ���s�v�v�B����æ����s���u���w�ǡv--�@�Ӧ^����v�{���V���v����з~���ݶi�Ӳ`�J�͵Ʀa�P���v�P�b���H����|��Ǭ�s���C
�m���̹���Ϸs�D�Ʒ~�n����25�~�ӧi�A�C�o�Ӿ��g�|�����@�@�������w�ɴ���s���G�A��M��ƶi�J�u���v�����v���ꥻ�P�f�O�C���F�s�D�v��s�������v�¤�~�_���ͭɧǨ���Ĥ�C���dzN�^�m�~�A�@�̩Ұl�D���A�O�@�������ø�����w�ɴ��s�D�Ǽ����骺�����a�ϡC�@�̥ؼЩ��T����s�o��F�@�ؤ��Z���dzN��ת�����C�o�D�n�����٤��O�@�̡u�i��`�J�B�t�Ϊ���s�v�]�u���סv�^���l�D�A���u�O�@�اƱ�P�l�M���ۥաC�o�̪��j��ק�h�����O�@�̹冀�w�ɴ�/���̹���Ϸs�D�Ʒ~���誺�M������P�H�ΥѦ��ӧΦ����j�Ŷ��C���Ӥ��b���~��A�@�̭n�٭쪺�O�u���̹���Ϸs�D�Ʒ~�O�s���D�D�q���s�D�Ʒ~�v�A�u���̹���Ϸs�D�Ʒ~�O����@���һ�ɪ��s�D�Ʒ~�v�A�u���̹���Ϸs�D�Ʒ~�O���̹���ϰ��F�~�l�B���餧�~���Ҧ����Ū��s�D�Ʒ~�v�A�u���̹���Ϸs�D�Ʒ~�O�ϫҤϫʫت��s�D�Ʒ~�v�A�u���̹���Ϸs�D�Ʒ~�O���ڪ��s�D�Ʒ~�v�A�u���̹���Ϸs�D�Ʒ~�O��Ǫ��s�D�Ʒ~�v�A�u���̹���Ϸs�D�Ʒ~�O�j�����s�D�Ʒ~�v�o�˪��H���ʪ��s�D�Ǫ��j����F���ӪŶ����y�z�A�u���Ѭ�s���O�b�G�Q�@���T�|�Q�~�N����_���B�̵ªF���B��L�F�n�����s�j�a��̡A����@���ҩҳп쪺�Ҧ����s�D�Ʒ~�A�]�A�����šB��_���B���̹���ϡB�U�Ӥ��ϡB���B�m�D�̰ܳ�h���������s�D�Ʒ~�A��Y�y���̹���Ϸs�D�Ʒ~�z�v�]�m���סn�^�C
�@�̧Ʊ檺���ز`�J�B�t�Ϊ���s�o��F���Ī���k������C�o���ȶȫ����O�@�̹�a�z�ǵ��dzN�귽���ޥΡA�ƹ�W�A�g�ѧ@�̱a��ڭ̦^����v�{���A�b�۵M�����B�F�v�y�ҡB�����@�����A�g�����̹���Ϸs�D�Ʒ~���a��ʸg��A�ҥH�A�ڭ̪��\Ū�g�礤�A�۵M�ӵM�a�֦��F��¦���X�o�I�A�]����Ӫ��U�ؾ��v�ʪ���I�]�F�h�˩ʪ��귽�ʥC�o�̧�h�٬O���g�Ѳ{��P���v����ܵ���V�����p�A�@�̩ҽᤩ�@�ӭӬG�Ʀۦp�}�Ҫ��h�˩ʤO�q�������o�����ޥ��C
�m���̹���Ϸs�D�Ǽ��Ʒ~�n�H�B����N�ڭ̱a�J�@�ӡu��q���v���@�ɨ÷P���j�����~�������H���ʹ�ܪ���ҩʷN�q�C�Ҧp�A����}�i���e���B�ʪ����D�A�@�̤��Ѵ��ܾ\Ū�̪`�N���P�A�~�^���嫬���D���������ʻP�өʡF����m��ϸs�����n�A�N�@�w�n�]�߱M������r�A�N�m�ѩ����n�B�m��ϸs�����n�u���m�@�B�v�]����ѻy�^�A�Y�{���̤������������ζǼ������v�����Y�A�ר�O�ܾԳӧQ�����������X�@�@�`�A�̬O���Ħa�Y�{�F���v�������ʥH�Ω��w�ɴ��s�D�ǴC��ƪ��гy��--�ɧU��h�E��m�ѩ����n���������Y�վA�A���Ȥ������۾DzߡA���O�a�P�i�F���̹���Ϫ��s�D���D�F��¶�m���Q�P�������n���Z�o�ƥ�A�z�L�m�ѩ����n�B�m��ϸs�����n�M���a�ݨ�F�ۨ����P�����F�ӽo�өP�Ԧa�Q���m�ѩ����n�B�s�ت��o�˪������C�������b���K���ɭԡA�@�̤��ѰO����ɧU��m���F���n�B�m�j�����n�B�m�T����n�B�m�������n�����лP���R�A�Y�㩵�w���g��M�a�誺�g�礧���s�b�ӫ�˪��L�����t���A�Ӧa��ʸg��S�b���Ǥ譱�гy�ʦa�o�i�øɥR�F���w�����o�˪��`�����j���D�C
�u�ڭ̵L�k�H��������T�רӴy�z��q���C�v �]�]���^�d�����DJ�D�֧J�����G�m��{�N���@��F--�ܻy���V�n�A���A����Ķ�A����H���j�ǥX�����A2002�A��104���C�^�M�ӡA���p�ڭ̩Ҭݨ쪺���ˡA�g�L���z���ŵ��P�S�O���Q�ơA�m���̹���Ϸs�D�Ʒ~�n�짻�ӤS�ӿ��a�e�{�F�����w�ɴ��s�D�Ǽ���ƥ��T�����dzN�����C�N���c�Ө��A���ܹ����������m���H�n�ɩһ����ܡG�u�e�����@�Ӥ��ХD�D���Ǽ֡C�c�����T�֪��O�X�Ӽֳ��A�C�Ӽֳ��᳣̫��D�D���ƤF�@�M�A�C�@�Ӽֳ������ۤv�����`�k�M��l�C�b�D�D���̥��@�������Ƥ��ᱵ�ӴN�Ӥ@���w�Y�� �B�M�Ӫ��צ��C���ӳo�تF�譵�֮a�]�\�|�����@�ӾA�����W�١C�ڤ��|�F�ڥu���D��Ū����ӧ@�~�n��ť�F�@���ީ��ֶ����j�t���C�v�]�]�w�^�|�D�ҡD���J���G�m���H�n�A�ڪ���Ķ�A�T�p�ѩ��A1985�A��225-226���AĶ�岤�����ܡC�^�̭��n���O�A���S���]�m�Ӧh�����c�W�h�A�]�S���b�J���W�h����U��²�檺�u�K�[�v�M���F�ۤϡA�ѩ�D�D����X�N�ѡA�m���̹���Ϸs�D�Ʒ~�n���}�ʦa�u�F�v�\�h�u�e�e�ʡv���귽�A�����u���w�ɴ��s�D�Ǽ���ơv���u���w�P�v�{�{�䤤���F��ʤ��e�A�B�̲ץͦ��C����G���K�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