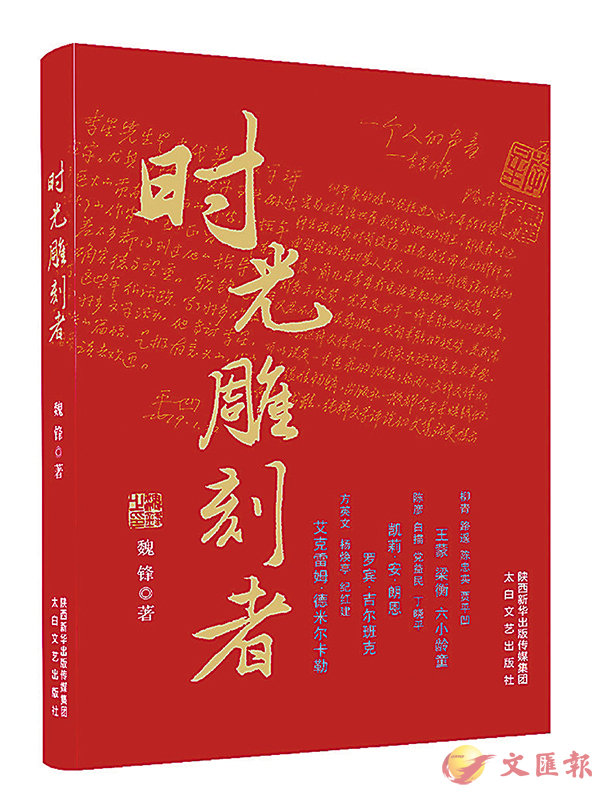
《時光雕刻者》
作者:魏鋒
出版社:太白文藝出版社
作家在大眾讀者心目中的形象,正在變得遙遠與模糊,作為一個身份、一種職業,作家值得崇敬的價值,也正在逐漸被時代所消蝕。如果把時代比喻作一座城市,那麼作家與他們的作品則是這座城市的一道古老的「城牆」,人們走到「城牆」邊上隨意看看,或者到上面隨便走走,然後便離開了,不留一句感慨。
試試看,當你在腦海中依次搜尋這些作家--柳青、路遙、王蒙、陳忠實、賈平凹等人的面容與名字時,會不會聯想到「城牆」或者其他類似正在變得古老而又斑駁的事物。可能你會反對:不是這樣的,這些作家雖然有的已經離世,但有的還正好好地活着呀,怎會像你說的那樣變得「古老」?可確實是這樣,我在閱讀魏鋒出版的書《時光雕刻者》時,真的體會到了一種正在貼近「城牆」時所能感受到的氣息--有着時光的沉澱,藏着思想的堅硬,散發着青苔般的清新--這些,都是在「古老」中生長出來的。
魏鋒是一名作家,但他近年一直走在追隨那些著名作家的路上,「有人在變老,但一直有人年輕」,對於著名作家群的追蹤與探訪,以及認真的記錄與書寫,使得魏鋒一直保持着年輕人的姿態與心態,他將書中寫到的那些作家形容為「時光雕刻者」是準確的--作家用文字記錄時光、留存人物、表達思想,他們就像執着而認真的匠人,一生從事着寫作這項艱苦而又有成就感的工作,為讀者留下一本本紙上「雕像」。而作為有志於要為一位位作家立傳的人來說,魏鋒也是一名「時光雕刻者」,隔着時光的兩個層面的「時光雕刻者」,形成了一種深邃的、令人肅然的互動關係。
魏鋒是陝西人,陝西籍作家是《時光雕刻者》的主角,魏鋒對他們有一種摻雜了崇敬的偏愛。陝西籍作家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和其他省份作家在成名後紛紛離開故鄉不同,具有代表性的那幾位陝西籍作家,彷彿生了根一樣不願走出那片黃土地,他們唱秦腔,吃羊肉泡饃,用筆講故事,那些個字落在地上,一個字就能砸出一個坑,儘管這個世界早已花花綠綠了,但他們的精神世界裏永遠有着一股拂之不去的蒼涼。
讀魏鋒筆下的他們,會時不時被這蒼涼驚到,四卷的《創業史》,柳青只完成了第二部的前14章,去世之前他期望女兒劉可風能夠幫他完成這部作品,或是為了激勵女兒,柳青說了這樣一句話,「女兒呀!你長了我的頭腦,血管裏流了我的血,但沒有我的精神!」,柳青還將收藏的一塊二戰彈片送給女兒,鼓勵她用鋼鐵般的意志去寫作......現在誰還會用戰士般的意志去寫作?誰還會把寫作當成一項未竟的事業期待子女去繼承?
為了盡可能將筆下的作家形象「雕刻」得更清晰、完整些,魏鋒往往會採訪三到四位與作家有着親密交往的人,因此他的《時光雕刻者》如同架設了三四個機位拍攝的紀錄片,有着動人的真實性與吸引力,為路遙寫傳記的張艷茜在與魏鋒對話回憶路遙時,就用口語化的表達講述了多個這樣令人動容的瞬間,「路遙去世後,有一段日子,我經常恍惚地感覺到,他還會出現在省作協院子裏......我會說,路遙,我要重新和你交往。」這樣的講述,很場景化,很有感染力,可是也因為具有明顯的假設性,讓人覺得傷感。
在刻畫筆下作家形象時,魏鋒是理性而克制的,他像是坐在攝像機監控器旁的「導演」,靜靜地觀看着筆下作家走出書齋,與他們的朋友、訪問者一字一句地交談着,這為《時光雕刻者》增添了可讀性,但同時也沒有損失該書的資料留存價值。簡而言之,這是一本「用筆有力道,情感有深度,表達有層次」的著作。
讀完掩卷,我感覺到自己彷彿在西安的古城牆上又獨自走了一圈,正是夏季,偶有雨滴,作家用筆寫他們生活的土地與城市,也用筆建築一道厚實的文學「城牆」,為的就是不管多久之後,讀者都能體會到這道「牆」的厚重。魏鋒既是這道「文學城牆」的雕刻者,也是守護者,他的匠人之心,保證了他有這個能力與水平。
文:韓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