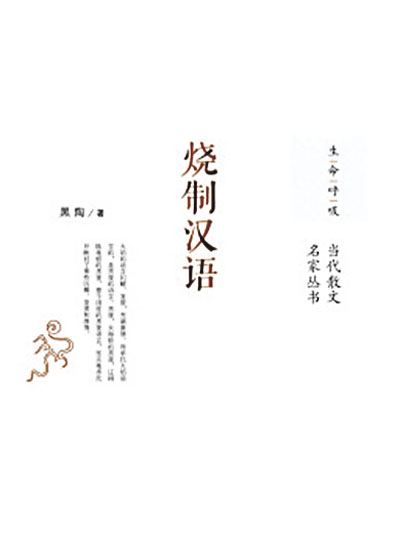 《燒製漢語》作者:黑陶 出版:東方出版社
《燒製漢語》作者:黑陶 出版:東方出版社讀這本書,有點像聽老友東拉西扯的嘮家常。總共412則片段式的劄記篇幅都不長,有的僅是一句話,但娓娓道來中,時時閃爍知識的光芒、思想的火花,使它又像一盤尚未打洞加工的珍珠,不會因為斷線而灑落一地無心的空洞。作者一再強調文字的根,作為陶都龍窯邊出生的孩子,他也像對待陶土一樣對待使用的漢字,要把它們打上自己的印記,然後放在窯裡燒出個性的質感。「每一個漢字,追溯其源頭,都充滿山河的氣息,植物的氣息,星辰的氣息,祖先活動的氣息。漢字是紛繁世界象形的轉述和凝定,色彩、音響、動作、情感,都涵納於簡潔的筆畫之中。」作者這份精神的傳承用在了對中國漢語的研究與熱愛上,使他「擁有漢字,感覺幸福」,並把這種幸福感傳達給了讀者。
我們日常所見的,無非是浮在生活表面的政治、經濟之類,而語言文字的背後,則是意識的反映,描寫的態度、動作、形象,則是人物靈魂的反映。漢字的使用具有「記錄交流層面、審美層次、創造層面」三個層次,「無數人共用着三四千個漢字,但在優秀作家那裡,他們就有功力能夠在這公用的幾千個漢字身上,深深烙上各自鮮明的個人印記。」這就是創造的魅力所在,一切藝術的真諦,都離不開激起想像和創造的激情,藝術在尋找某些象徵性的同時,也是在尋找現實的出路。「中國傳統文化依然存在大量我們至今未解,或者我們至今只窺其形、未懂其的神秘資源」,這就為我們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料,那些所謂流行,都是小市民的被動習性,有主見的人一般都拒絕不曾沉澱的流行,所以,「一個作家的信念、操守、沉默的力量以及內心對理想的執着與捍衛」,使他在孤寂中「享受着秘密的創造的喜悅」。因為「顯赫或孤獨,榮耀或歧視,主流或邊緣,權貴或平民,所有這些作品之外的東西,時間終將它們沖刷乾淨......李賀與韓愈,在後世的閱讀中,他們並沒有身份的不同。」所以他相信火焰般發燙的文字,必然會把那些「儘管『妙趣橫生,古怪精靈』,儘管『慧黠機巧,天馬行空』,終究是不具備價值的泡沫」蒸發掉。這是需要定力的,正如他說讀書破萬卷的三個層次:「第一層意思是破爛之破,用功勤奮,將書翻破了。其二是破解之破,即讀懂、破解。第三則為突破之破。突破陳舊,完成自我。」
物質文明在突飛猛進地發展,而發展總是伴隨了破壞,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的均質空間,會使人最後產生無處可去的孤獨與絕望,絕望地走向簡單的死亡。沒有故鄉溫馨的家園,也沒有精神威嚴而美麗的靈魂,世界只是不同物種的消亡與變遷,人們卻都急於改變自己在地球上同伴中的地位,少有閑情用文字來溫潤自己。水泥地覆蓋了土地,機械生產使人類趨於機械化的生活,財富的增長也使財富的佔有者感到需要佔有比前人更多的財富,才能免於淹沒個體的存在。也許「燒製」出來的文字,因為追求質感而弄得易於脆損,以至於最終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一直到很久以後,或許才偶爾會有被人發現其碎片具有價值的機會,但至少它可以用來撫慰當下自己精神家園的荒蕪。
生命的地平線,如果一馬平川,就難以產生美麗的思想光輝。作者敘述了苦難所反彈出的能量,因為幻想的絢麗程度與遭受過的艱難困苦成正比,所以那些曾經的不平、窘迫、耳熱心跳、喜怒哀樂,都是一輩子值得珍惜的燃料。點燃了的窯火,照見淺薄者在用冷漠的外衣緊裹一顆脆弱而緊張的心,他們的謊言裡其實也包含着可憐的希望,不必打碎他們的夢,讓他們用這可憐的希望之盾,去抵擋一陣無聊的空虛好了。現實與虛構,合理與違理,善和惡的分界線從來不甚分明,只是不懂幸福的人永遠追求那些金錢、名聲等等誰都知道的東西,等到妄想膨脹了周圍的空氣,物質成了唯一的動力,去何處尋找自己?而懂得幸福的人,又多半是他們無法理解的人。■文:龔敏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