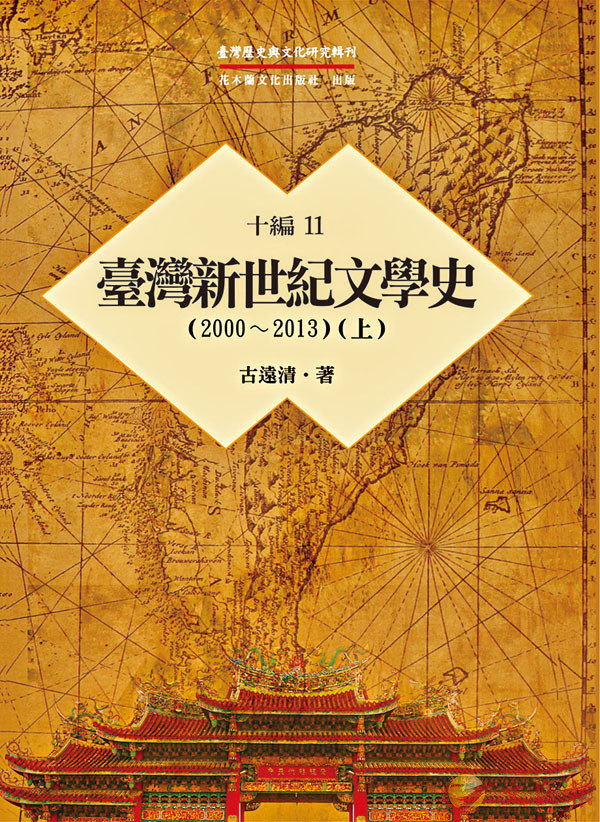
──讀古遠清《台灣新世紀文學史》
古遠清以研究華文文學著稱於學術界。他和劉登翰一起被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稱為最有影響力的台港文學研究者。與劉登翰不同的是他走的是私家治史路線,且不以微觀研究行世,而以境外文學史撰寫著稱。《台灣新世紀文學史》,便是他獨立寫作出版的第八部文學史。
千禧年鐘聲的敲響,帶給人們的不光是物理時間上的新起跑線,更蘊含着人們對台灣新世紀文學的希冀與期望。作為一位有20年「工齡」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且偶爾寫點文章參與台灣文壇論爭的大陸學人古遠清,他感到越來越需要研究新世紀台灣文學有哪些新氣象、新情況,尤其是當民主選舉成為台灣「聖牛」情勢下的當前文學,對正在自我矮化、自我村落化、鼓吹用「台語」取代漢語、用「華人」取代「中國人」的本土文壇,的確很需要跟蹤書寫。
在內地學界,新世紀文學是一個熱門話題,可對台灣新世紀文學,鮮有人問津。就是對岸的學術界,也沒有人做這方面的系統研究。可以說,基於對新世紀文學研究現狀尋求格局的改觀和獲取新的學術生長點,是古遠清寫作《台灣新世紀文學史》的主要動力。
台灣文學研究本不應陳陳相因,而應在創新上下功夫。在《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序言中,古遠清開宗明義「用政治天線接收台灣文學頻道」做標題。也就是說,基於台灣新世紀文學與政治難解難分的關係,古遠清對以往的純文學研究方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研究台灣文學尤其是新世紀文學,不能只有審美標尺,還應該用「政治文藝學」的方法去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台灣新世紀文學的特質,才能把握台灣新世紀文學與上世紀文學的不同之處。這不同之處古遠清概括為:「新台灣寫實」及新鄉土小說的誕生、「後遺民寫作」、奇幻文學風潮、小說中出現的「後人類」情景、典範轉移與作家全集出版、《台灣文藝》吹熄燈號、副刊的娛樂性和話題性在擠壓文學性、散文與小說界限不清、「同志文學」熱潮降溫、後殖民理論式微、國民黨遷台一甲子的歷史記憶以及馬華作家在台灣的論述 。所有這些,導致「台灣新世紀文學」和20世紀台灣文學的不同在於期盼從文本到語言的激烈變革;期盼副刊格局不再固定於《中央日報》守舊、《中國時報》前衛、《聯合報》持中、《自立晚報》本土;期盼從形象塑造到文壇結構的重新洗牌;期盼用散文尤其是回憶錄去取代小說的霸主地位;期盼長篇小說時代的來臨;總之是期盼突破上世紀文學的規範和權力分配,期盼在創作上尋找與新時代相適應的表達方式。
寫文學史,不僅要有出色的史筆,而且更重要的是應有新穎的史觀。是這種史觀,決定一本書品質的高下和優劣。目前在台灣最流行的是本土史觀,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新文學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文學。可是當古遠清回溯台灣新世紀文學發展歷程,尤其是新世紀出現的後遺民寫作、回憶錄寫作潮時,發現這種單一的本土史觀會帶來的諸多局限與制約。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古遠清堅持大陸學者的立場,同時立足於台灣新世紀文學本身,使他能有效地還原當下台灣文學現場,破除後現代後殖民這些西方文藝理論對台灣文學研究宰制所帶來的尷尬,廓清種種本土化理論的迷思與遮蔽,從而接近台灣新世紀文學發展的原貌,真正實現將分流的兩岸文學加以整合。關於這一點,在《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導論的第三節《兩岸文學,各自表述》,已有生動闡明。正是基於內地視角和內地主體性的堅持,才有《三分天下的台灣文壇》《由「台灣的文學年鑒」到「台灣文學的年鑒」》《「台語文學」的內部敵人》這些精彩篇章的產生。
《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另一特點是不受「大敘事」的局限,注意細節的發掘與展示。古遠清靠《印刻文學生活志INK》中的「印刻」之名的由來這些細節,編織出多層次的文學史現象。這是一本有故事的文學史,如「文學事件」中對杜十三「行為藝術」的敘述,對「上官鼎」這位武俠小說家筆名的解讀及其代表作的分析,還有稗官野史的運用,貌似守舊,卻讓這部文學史生動有趣,讀起來不至於枯燥無味。
總之,古遠清用真誠、善意、犀利的文筆,記錄與評價新世紀台灣文壇洶湧而來的政治小說、波瀾壯闊的回憶錄以及長流不盡的各種創作。他用一顆端然中帶有迷惘但決非沮喪的心,書寫着台灣新世紀文學走過的旅程,其中包括收穫、焦慮、爭辯、遺憾與歌哭、欣喜和感動。這裡有電閃雷鳴般的文學事件,更有雲淡風輕般的審美愉悅。從彼岸走向此岸,從台灣返歸內地。古遠清將這部分上、下冊且全精裝的《台灣新世紀文學史》,獻給台灣的文朋、詩友,以及所有關注台灣文壇最新動向的學者和讀者。■文:曹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