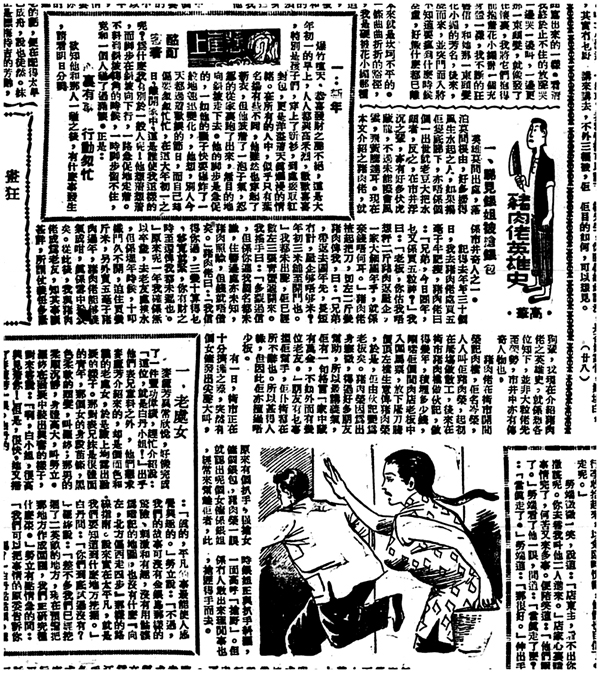 ■高華即江之南的三及第小說。 作者提供
■高華即江之南的三及第小說。 作者提供黃仲鳴
記得當初閱讀三及第(廣東話、白話文、文言混合而成的文體)的作品時,便驚訝它語言的特別,絕非貼近我們生活的語言,尤其是三及第作品中的對白,更是「堅離地」,如凌侶即高雄的《香港靚女日記》:
「我曰:『我只怕做唔來耳,你如果認為我做得到,我就試一下,未知幾時開始?』張阿拔曰:『你肯,即刻開始矣。』我曰:『今日就開始耶?』」(《明報》,1959年6月8日)
對白中的「耳」、「矣」、「耶」等文言虛詞,絕不會掛在現代人的口中;因此,這只是書面語。而這類虛詞,廣見於三及第作品中,連市井人物也「之乎者也矣」個不休,如高華刊於《明報》的〈豬肉佬英雄史〉:
「大頭森曰:『唔係有人恰我,而係有人想找你晦氣也。是否你昨早打過一個扒手?』你豬肉榮曰:『冇錯,有條衰仔搶銀包,被搶銀包個銀姐,係我豬肉檔之客仔也,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乜現在呢個賊仔要報仇乎?』」(《明報》,1960年3月7日)
大頭森是燒臘檔伙記,豬肉榮是賣豬肉的市井人物,對白居然「也乎」一番,這絕對不是生活的語言,也不符講者的職業和身份。這類對白中的虛詞源自古典的文言小說,一路傳下來,成為三及第作家的「經典絕句」,沒有了這些文言虛詞,便不成為三及第。後來有些粵語入文的作品,將這類虛詞全換上「啲」、「咩」、「咗」、「嘅」,便無文言虛詞那麼典雅和有韻味了,如:
「佢見到我咭片上嘅Title,呆咗一呆,話:『估唔到你撈得咁掂!』我亦都唔想多講,拍一拍佢膊頭,話:『第日出嚟飲茶!』」(阿寬的《小男人周記》)
其實,三及第雖夾雜粵語,卻是頗雅馴的書面語。有一個疑問是,三及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為流行,一般報刊和書仔夾雜大量的文言,在白話文普及下,市民竟大都能看得懂,真是奇哉怪也。
說穿了一點也不出奇。第一,辛亥革命後,遺老、舉人、宿儒,大量湧聚香港,與官紳掛鈎,提倡復古,抵制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拒白話文,書塾紛紛成立,力倡古文;第二,當時的港英政府,為了阻止青年學生自覺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刻意維持半封建殖民地局面,於是極力推行古文,更強迫使用《香港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德政。第三,坊間的新文學運動書刊太少,有的是鴛鴦蝴蝶派,而這派的作品,大都是以淺白文言所撰;第四,當時報刊的文章,多以淺白文言行文;諧部文章,粵謳、南音、龍舟等說唱文學充斥。有此四大背景和「閱讀傳統」,普羅大眾自然看得懂。加上行文中還加上了廣府話,令他們更覺親切;所以三及第能夠大盛,不無因的。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類作家、文人退役或逝世了,讀者也老去了,三及第就衰落下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報刊上得睹這類文體者,唯吳昊、韓中旋、沈西城、吳敬子而已。
